阮清越 (Viet Thanh Nguyen) : 读《爱的彷徨》 辨亚美文学之声
作者:阮清越 (Viet Thanh Nguyen) 译者:黄清华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singhua U 清华大学语言中心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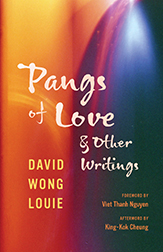
雷祖威的首部作品《爱的彷徨:短篇故事集》出版于1991年。如今,至少每个月都有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出版,但在当年,新的亚裔作家崭露头角可是一件大事。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书店的一张桌子上看到此书首版精装本,立刻满怀热望地买下来。虽已时隔二十七载,当时的场景却历历在目。那年我二十岁,与亚裔美国文学、亚裔美国研究的邂逅彻底改变了我。我是在之前一年抵达伯克利的,当时只读过谭恩美。在伯克利,我很快读完了汤亭亭、赵健秀、任碧莲、戴维·穆拉(David Mura),还有冯黎莉(LeLy Hayslip)。之后不久,我便围绕亚裔美国文学开始了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这篇后来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的文稿像一颗种子,渐渐成长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我的第一本书,并最终开启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之所以提这些,是想说,当年拿起《爱的彷徨》一书的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年轻学者、皈依亚裔美国事业的狂热信徒。接近此书时,我还只是一位初学写作者、一个局促不安的家伙、一名刚入行的亚裔美国研究者。与祖威的小说相逢之时,正是我深陷艺术漩涡、政治迷局而无力自拔之日。21岁的我年轻气盛,对自我信仰以及自己看待世界、看待文学的方式执迷不悟,所以,《爱的彷徨》令我一头雾水。故事很棒,这一点我非常认可。但是,这些故事寓意何在?为何要在寿司店的恒温水箱里放一只水獭?为何如此多男性失意落魄?究竟如何定义爱之彷徨?那时的我尚不解生命中所蒙之爱,亦不知何为施爱与人,所以,尽管我知晓书名的字面意思,但爱的彷徨究竟作何感受,尤其对那个不懂爱、也不会爱的我来说,尚不得而知。
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审美、政治层面上,二十岁的我还无法读懂《爱的彷徨》。那时的我一心幻想着要当作家、并醉心于校园运动,这本小说集对我来说过于睿智、过于老练、过于深刻、也过于成熟。我想要的是一本有关亚裔美国的书,而祖威的书既是、又不仅仅是一本亚裔美国书。书里着重描写了一些亚裔美国角色和亚裔美国主题,比如那些最终沦为不合格的恋人、不称职的父亲、以及可笑失败者的落魄男性。此类人物在汤亭亭、赵健秀、任碧莲的作品中也不陌生。除此以外,《爱的彷徨》还涉及中国政治动荡的深刻烙印、讲述与古长城修建有关的充满弦外之音的传说。祖威甚至为书中某些角色取了类似爱德赛(Edsel)这样的名字,听上去特别土,因为我的华美朋友中也真有叫威尔森(Wilson)、波拿巴(Bonaparte)的。
在祖威的文集中,有一些故事虽取材于华裔美国社区,但其主题却并不局限于华美圈。例如,第一个短篇小说《生日》的主角是华莱士·王(Wallace Wong),故事主要讲述他在美期间如何拒绝摒弃一些中国想法及陈年旧物。王先生是华裔美国人,开了一家意大利餐馆。故事中对于族裔、文化及两者间密切关系的描写,无一不是为了衬托王先生那自以为不足的男儿气概,以及对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孩视如己出的父爱。围绕“父亲”、“儿子”、“情人”等社会角色的探讨贯穿着整本文集。祖威心怀悲悯、目光敏锐,将这些普遍性经验表达得精妙绝伦。但于此同时,他也勇于把美国华人的独到情怀赋予这些普遍经验。
20岁时,我学会了应用亚裔美国视角看问题,但可能当时我过于注重华裔美国视角,所以无法像今天这样理解祖威所探索的其他角度。采用多重视角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绝非易事。在花了17年时间完成一部短篇小说集后, 我才最终体会到这一点。多年前,我忽视了祖威小说中的两个独特视角:一为荒诞,二为幽默。在此次重读过程中,我才发现这些故事往往特别搞笑,有时又很诡异,当然,我指的是正面意义上的搞笑和诡异,这一点在水獭的故事中可见分晓。在这篇名为《数瓶薄酒莱葡萄酒》(Bottles of Beaujolais)[1]的故事中,气候学家企图引诱那位迷恋水獭的女士。他在笨手笨脚切寿司时割伤了手,而他的情人则上前挤压他的伤处并把鲜血滴进一瓶日本米酒,从而令米酒变身“薄酒莱”。他们将这混“血”文化结晶喝掉,然后带着水獭一起钻进出租车远去。何其诡异。
身为文学评论家的那个我会说,水獭代表了他者。这个他者经常出现在祖威的故事里,通常象征着身为他者的焦虑。这些焦虑有时关乎种族、文化或国籍,有时关乎自己与所爱之人或应爱之人无法沟通之苦闷。不过或许我不应过度解读。毕竟,在《社会科学》这一故事中,像我一样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也遭到了讽刺。在这个有些伤感又有些搞笑的故事里,一位神秘的学者企图购置另一位学者(即主人公亨利)的房屋并同时迎娶那位学者的前妻。那亨利先生曾经“在研究所接受过‘透过文本看本质’之学术训练”,因此,在某次读到一篇题为《如何制作瓜球》[2]的学生论文时,他一口断定那学生对他有意。但是有时候,球不过是球,水獭也不过是水獭而已。难道不是吗?
在以上短篇及祖威文集中的其他短篇中,爱的彷徨多源自失败之爱、失意之爱和失望之爱,有时关乎家庭,有时关乎情爱。家人之间疑虑重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来就容易令人困惑,而这种困惑如果发生在在华人家庭就会变本加厉,因为就期望与预期而言,身为移民的父母与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的子女往往背道而驰。在《爱的彷徨》这一故事中,庞太太去看望事业颇为成功的小儿子,恰逢儿子的朋友们来访。她注意到来访者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便问大儿子:“这些男人都有体面的工作,又有钱,为什么身边没有女人?你弟弟为什么那个样子?他怎么跟你说的?我真搞不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同性恋儿子却是整本书中为数不多的在爱情上取得成功的角色之一。对于大部分故事中的其他角色而言,个人天地正在坍塌或者已经坍塌,身后的情感关系一片瓦砾。有一个故事取名《加冰块的爱情》,讲述了一个失败的情感故事。——我的老天,这岂止是失败!——当你看到结尾处那令人震惊的一幕,会忍不住目瞪口呆。假如用《加冰块的爱》来做整本小说集的名字,似乎也挺合适。
在寥寥可数的爱情关系还算正常的故事中,其他某种故事元素却又糟糕透顶。以《一个20世纪的男人似真似幻的彷徨》为例:该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看上去还可以,但不幸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却彻底失控:核导弹与原子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假设我们把核毁灭偷换成“气候突变”或“国内政乱”,会发现故事所隐喻的痼疾完全应景,尤其是当我们读到“在刚结束的选举中,妻子和我选了一大堆一败涂地的家伙。尽管选举令我们的朋友们愤愤不平…但其实我们从不相信任何一个政党能救我们。”听起来耳熟吗?故事的主人公既是该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创作该故事的作家。在他看来,无论是可能出现的世界末日景象,还是国内沉闷的政治局面,都可以通过诗歌和写作予以改观与重塑。且不说是否过于天真,作者的愿望是,通过文学艺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为应对世界末日做些准备。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自然信奉这样的乐观主义或天真。通过对祖威作品的重读,我更坚信自己的感觉,即艺术是重要的,写作是重要的。祖威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仿如昨日刚刚写就,便是证据之一。这些故事在今天依然有力、依然感人、依然切题、依然迫切;它们恒久的生命力源自作者的想象力及讲故事的能力,源自他的智慧、幽默、以及直面人世之黑暗与人性之曙光的意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处理文字的方式。在《传承》(Inheritance)一文中,叙述者提到:“我记起曾有人在一本图书馆的书上草草写了一句颇具远见的话:我们的未来掌握在孩子手中,”但是“手”一词却被不知什么人涂鸦成了手枪的样子。这个故事写在哥伦拜恩高中枪击事件[3]、以及之后发生的多起校园谋杀案之前,充满令人不安的预言性,但是,在面对世界末日之时,我们只会恐慌、哀悼和愤怒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文字、善用文字。
通过他自己生命的后记,即《此吃成追忆》一文,祖威最后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作家的使命。对大多数作者而言,这是我们首次获悉祖威与喉癌之间痛苦而持久的抗争。说话与吃饭这两项与生俱来的技能,赋予我们愉悦以及表达自我的能力,可祖威患上的喉癌及其治疗方案却剥夺了他的这两项技能。然而,即便此时祖威已无法讲话,他仍在坚持写作。同为从事写作的人,我在读这篇文章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位医生在观察患者的画面。患者的人性、需求、痛苦都在观察之列,这是自然,但医生在观察患者身体时还有一层临床治疗任务。与大家一样,我也感动于祖威的病痛;但我同时也注意到,促生这动人行文的是祖威的艺术,而体验这种艺术本身又是令人向往的。这是写作的矛盾功能——于作者、于读者皆如此——即艺术可帮助我们把痛苦的刻画得扣人心弦,也可帮助我们去想象那些难以想象的。
有时难以想象的恰恰是身边人的痛苦。对《爱的彷徨》的读者来说,祖威巧妙地刻画了他笔下诸多角色的痛苦,而在《此吃成追忆》中,他自己成了被刻画的对象。就风格而言,这篇散文完全可收入他的短篇集。文中的“彷徨”之源,是身为作者、角色双重身份的祖威从此再也无缘品尝美食、再也无能进行咀嚼与吞咽、再也无法与家人共享一日三餐。当然,文中所表现的“彷徨”也包括爱的彷徨,因为美味与家庭、社区、爱恋息息相关。正如他的妻子,每次都需要花几个小时,把食物精华挤成汁,然后用一根很细的导管喂给他喝。他们曾经分享和眷恋的关于一日三餐的记忆,既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尽管祖威当时已无法再享用美味,且不得不忍受其他食客向他和插入嗓子的导管所投来的异样目光,他和妻子还是决定带女儿去一家新餐馆,试图重新唤起往日美好记忆。“那晚拍摄的照片里,女儿看上去好可怜。九岁的她,已学会如何在镜头前用笑容掩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她的眼神却暴露了餐桌上所有人的心情:但愿我们都远离此情此景。”这令人心酸而又荒诞的场面,凸显了父母、子女、以及情人们之间尴尬的爱。而这,正是祖威用他精湛的行文技巧、敏锐的感知力以及出色的同理心在《爱的彷徨》一书中反复探讨的。
身为作家,我认为——同时也希望——写作的益处之一是能够帮我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赐予我必要的智慧,或起码拥有智慧的幻觉。当我想象处于极端环境的角色时,我意识到我如同身临其境,正在为面对自己的生命尽头做准备。我希望自己在生命终点来临之际,能够做到像为一部短篇小说收尾那样,走得泰然自若。
作为一名写作者、同时又是祖威及其作品的爱好者,我愿意相信,他的艺术已为他赢得了面对死亡的坦然。他的文字、他笔下那些关于别人和自己的故事,是我和大多数读者作出如此判断的唯一证据。我们这些喜爱祖威作品的人,无论是文学爱好者、作家、还是普通读者,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艺术存在的必要性、相信文学的永恒、相信笔下人物可经由写作者大脑中的魔法而变得栩栩如生。如果这些笔下人物并无多少真实性可言,我们何以一遍又一遍地拜访、重访他们呢?这些寻访告诉我们,生命虽有限,角色却得永生。故事长传。
(非常感谢张敬珏、张黎为译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1] 薄酒莱:一种酒,来自法国勃根第地区南边的BEAUJOLAIS区,法语发音为Boh-Zhu-Lay, 一般将之译为薄酒莱,字义正好如何该酒清淡的口味。
[2] 原题为“How to Make Melon Balls”。”melon balls”在英文中是双关语,也用来指男性睾丸。
[3] 此处指1999年4月20日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的恶性枪击事件。凶手为该校两名18岁高中生。




